注册时间2007-12-10
最后登录1970-1-1
在线时间 小时
主题
精华
积分35
贡献
ST
道具劵
|
马上登陆,参与交流。无法注册或登陆请加QQ群:777694204 或Email:admin@cnkeyboard.net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帐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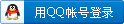

x
父亲的钢琴“VICTOYR"就是一只大魔术合——我小时候就这样认为;当我在它身上无意识地双手乱按,在我随意弄出的这一片噪音中猛然蹦出一声美妙的谐音时,我就得出这一结论。这是我最初的音乐感觉,这让我既着迷又惊奇。而“VICTOTR"这只大魔术合则让我感到敬畏。
我的家在市北区一处有十个小房间的独立院子里,因为父亲爱音乐,家里有钢琴,风琴,小提琴,还有一只单簧管。书籍也很多,其中印刷最精美的是父亲的圣经及宗教读物。在父母众多的孩子里我最小,所以一直得到哥姐的呵护,及父母的格外宠爱。孩子们都受过程度不等的音乐教育,我也不例外。我的钢琴教师是一位牧师——早年是神职,建国后靠教授钢琴和小提琴谋生。在我去董牧师家上课前,姐姐已经教我弹了好几册“汤普森”。每个星期天我都到董牧师家上课,他家那座二层的红瓦尖顶欧式小楼就在信号山一侧的齐东路最上端。
那时的我无忧无虑。每天完成学业后找一个僻静处悄悄地看小说是我另一大爱好“一千零一夜”“安徒生童话”“斯巴达克斯"就是这样看完的,漫画家布劳恩的“父与子”那可是我特别喜欢,能让我在梦里都笑出声的。。。
风和日丽的星期天, 父亲经常带上那架“蔡斯”相机,招呼一家人到海边,公园游玩。那时的我常常得到夸奖,当然大多来自家庭以外,有亲戚,父母的朋友,邻居,也有路人。他们大多说一些什么:有福,聪明,长得好看之类的话。还有人说一些逗趣的话,善意的恭维话。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有人拿我幼儿园时的小朋友,一位姓赵的长得极其漂亮的小女孩说事,那位有一对酒窝的小女孩可是个被娇惯坏的小公主。他们挤眉弄眼,添枝加叶的戏说我俩,弄得我面红耳赤,羞愧难当。又气又急地为自己辩护之余我竟然还有点得意,感到自己有一些与众不同,多多少少有一点飘飘然。
不过,这样的场景注定不会长久。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正在悄然逼近,它所掀起的狂涛必将粉碎我面前的生活。在这场由伟大领袖亲手发动的,十年后被称为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,有些倒霉蛋早就被预先盯上了,他们将被架在火上烤炙,然后送上祭坛供众神享用。在这场人肉盛宴中被摆上祭坛的就有著名的政治家刘少奇,邓小平,陶铸。。。至于被无产阶级视为阶级敌人的阶级异己分子,“封”“资”“修”分子。。。还有一些与马列主义,毛泽东思想不一致,与文革领导小组不一致,对党的方针政策,对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有疑问的人——这些人在教育界,学术界,文化艺术界,宗教界,民主党派,总之,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大量存在。可悲的是,这些人还往往是些忧国忧民的人,他们爱思索,也爱提意见,喜欢舞文弄墨,这些有点天真的,不知天高地厚的人,往往不明白自己是怎样得罪的尊神。在这场盛况空前的人肉盛宴中,他们也都是不同口味的主,副菜。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人则是这场盛宴中的调味料。
在随父亲被放逐的日子里,我有幸领略了贫下中农的教育。这有别于工人阶级戴高帽,挂木牌,游街示众,使用大头棒宽皮带的教育.这是一种阴柔性质的教育。我在接受教育中不但被“触及了灵魂"还熟练的掌握了多种技艺。在无休无止的劳动和无数次的体力透支后,套上挽具我就可以代替毛驴,拿起农具就是真正的荷锄农夫,抄起一人多高的马牙锯我就是解木人,将衣服脱剩个裤衩,蹬上防烫的木底鞋和皮巴掌,从余火未烬的窑洞里往外掏砖,我就是一个出陶工。。。我学会了在严冬长时间的外出劳作时,用一根宽布带包一只饼子系在贴肉的腰间,这样当我饿了时就可吃到温热的东西而不是冰饭砣;我也记得在炎热的夏天要随身带几瓣大蒜,当我渴极了又找不到清洁的水源,捧几掬沟渠的水喝时,用它来解毒。我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小少年改造成一个真正的无产劳动者,可我并没获得信任。
收到的信件经过了暗地检查你不能问;不定时的访客你不能拒绝——那是背着步枪的革委会治保干部和基干民兵专在夜深人静时的访问,刺眼的手电光直射眼睛,被窝里你得睁开眼睛,让访客们验明正身。我可不是令人敬佩的老舍先生,老舍先生在遭遇首次践踏就愤然投湖以死抗争,践约士可杀而不可辱。我选择做阿Q,我在心里愤怒着,事实上无语并顺从,我可以做懦夫,但我不摇尾乞怜。
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,我同多种眼神对望过。有几种眼神不能忘却 :一种是刀片一样冷酷的眼神——这是坚定的革命者,尽量不与之对视——会激发仇恨,引来暴力的,最好视而不见;一种是幸灾乐祸的眼神——这是痛苦的玩赏者,这种人有点卑怯,虽不会对你当面下手,但背后爱搞动作。这种人最可能成为落井下石者和为虎作伥的人。我同这种人对视,是因为我对其骨子里的蔑视与不屑,至于后果就顾不得了;还有一种是同情的眼神——这是天性善良的人,这种人眼里流露出的怜悯是人性中的至美,我却不敢对视。
“不是爱风尘,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,总赖东君主。。。” 可怜的严蕊在冤狱后终获“东君”释放,而我的“东君”是谁?毛泽东?他的后任妻子,文革小组的旗手江青?
一天一天,是那么漫长难熬,一年一年,仿佛一个一个世纪,心情憔悴而暗淡,几年过去我渐趋绝望。将终老于此矣!上头说得再清楚不过:“我们要将他们打翻在地,再踏上一只脚,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。” 我再也不能回到过去的世界了,再也不能夏天泡在海里嬉笑,秋天钻到山上粘知了,再也见不到“VICTORY”,再也不会有音乐,也不会有书籍了。。。
命运是多么不公!如果我生于工人家,或贫农家,就不会有这么多痛苦,这么多羞辱。这可不是由我做主的。我不能选择生,我只能选择死。我还不能死。之所以这样是有原因的:其一是本能的坚决抵抗。其二是我不甘心。我这么年轻,我还没尝遍生命的全味!就像是一个花蕾,就让它怒放后再凋谢吧!斯巴达克斯赴死前留给他的情人范莱丽雅的绝笔信,最后是这样写的:“。。。现在我要对你做最后一次亲吻,我要对你做最后一次想念,我的心脏也要为你做最后一次跳动” 年少时的我读到这里曾洒下过泪水。这是另一种情感,一种我不曾领略过的情感。其三是最重要的,就是我要等待,等待着直到有一天能洗刷掉我身上本就没有的所有耻辱!索回我本不该被剥夺的全部尊严!
我的苦难是因为与血统有牵连,父亲的苦难是因为与资本有牵连,这是一个连环套。在我最痛苦的时候,也曾怨恨过父母,幸好,这怨恨只持续了一小会。良知告诉我,他们都是好人!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液,我的脑袋里灌注着他们的思想,我也是个好人!他们追随基督的精神,希望用爱来拯救世界。冀望有一天这个世界充满了爱。他们读的圣经里有这样的话“爱是恒久忍耐,爱是永不止息”。。。我想象着世界上没有了恨 ,充满了爱,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。。。可那不过是幻影,就如水中月,镜中花。在眼前,更是可笑的一厢情愿。
一九七六年传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,不久又传来江青在内的“四人帮”被捕的消息。绝境中的人终于见到了一丝曙光 。两年后,政策发生转变,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。大批无辜的人被解放,国家从“人治”走向“法制” 那么多的人喜极而泣,我这个倒霉蛋也在其中。
我也得到了国家的补偿,被视同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就业,并从我年满十六岁起计算连续工龄。这有些讽刺的意味,但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知道,有些人就没能等到这一天 。就像遇罗克——这个当年名牌大学的高材生。他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而参与到“血统论”的辩论中。怀着年轻人的单纯和热情,及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,他像极了被绑在火刑柱上的哥白尼,也像极了虽九死终不悔的屈原。这使得他被过早枪毙。平反昭雪后,他没追称为“伟大的先觉者” 这是多大的悲剧!
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钢琴老师。那座尖顶的欧式小楼还在,只是故人不在。有人说他也被遣离本市,后来就客死他乡。
“夏天的飞鸟,飞到我窗前唱歌,又飞去了. 秋天的黄叶.它没有什么可唱,只叹息一声,就飞落在那里” 伤痕累累的“VICTORY" 回来了,十数年的分离,有隔世之感。其它的老相识都散失殆尽,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我粗硬的双手沟壑纵横不逊于任何两只熊掌,抚琴唱歌的雅事再也不能胜任。
......现在,我把"VICTORT"交给了我的儿子,就像当年父亲将它交给我。我没有用“VICTORY"完成我的钢琴学业,我的儿子却用修复后的“VICTORY"完成了他的钢琴学业。儿子学琴之前,第一木器厂的一位漆工——我朋友,要为“VICTORY"整容,他承诺褪去原漆后将重现原木的漂亮花纹,也可以染色,重漆后可以达到镜面效果。我没同意,让它保留这身伤痕好了,能让我记起什么,记得什么。乐器厂的调律师来做维修时提议用一架 国产的“珠江”或“聂耳”牌钢琴来交换“VICTORY"。我动过心 ——毕竟维护一架旧琴要费力费心。可我怎么忍心呢,“VICTORY”就像我的旧友,它若有知一定会难过的。儿子学琴的后期,他的钢琴老师王重生为“VICTORY”介绍了一位北京的调律师。这位长者将琴拆卸检查后提出两种方案,一种是长期的 :换一套新琴铉,全面调手法。一种是短期的:换部分锈蚀的高音区琴铉,个别调手法。他认为这琴值得大修,但他要预先备好整套的琴铉。我选择了后者。
中学时,儿子厌倦了钢琴,改玩手风琴。大学毕业后,他要做自由的职业音乐人。现在他已经有了“YAMAHA"和“KORG”,“VICTORY”则被冷落了多年。现在的“VICTORY”因为失修,跑调严重,有几根断铉,也有几个晃动的榔头。“VICTORY”年已老矣!
我所居住的老楼也已残破,政府已将它纳入拆迁规划,一旦真的拆迁“VICTORY”怎么办,怎么寄存它?带着它又太大太重,最少两次的搬动对它的身体也有较大的伤害。
在我将“VICTORY”交给儿子之前的几年里,我对它做过这样的最终设想:用它苍老但仍美丽的外衣做一张餐桌,用它金红色的钢骨架做我墙上的挂饰。这对我不是什么难事。不过,让它以这种方式做我对它最终的纪念未免有些残忍。我正值知天命之年,将步我父亲的后尘渐渐的接近我最后的终点,“VICTORY”总有一天要同我告别。同我父亲一样,我的旧友与我也有某种相似的东西,一种忧郁,伤怀的,器质性的东西。类似蓝调音乐,类似舒伯特的“晚安”和“菩提树”,类似福斯特的歌曲。。。。 |
评分
-
查看全部评分
|
 /2
/2 